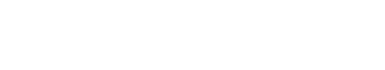2018年5月27日,14:00,田家炳书院204,45名学生,3位老师,120分钟。
这是2018届本硕博毕业生的最后一课。

在这最后一课,陈强老师用一节文学鉴赏课提供了一个追思“我是谁”的视角。
顾晓燕老师用丰富的个人从业经历告诉即将走向社会的同学们“要到哪里去”。
李红涛老师回忆了他19岁起踏入大学之后的求学岁月,与在座共同思索“我从哪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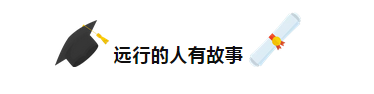
陈强,笔名“江弱水”。学生们对弱水先生的课,有八个字的评价:“娓娓道来,如沐春风。”在最后一课上,陈老师的语速依旧不疾不徐,语调依然抑扬顿挫。

和平日上古典与现代文学的课一样,他用文学作品来铺陈,引用了奥利弗·萨克斯的小说《错把妻子当帽子》:“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叙述,它不断地、无意识地被我们构建……在生物学上、心理学上,我们互相之间差异不大;而在历史上,作为叙述——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肉体归于泥土,每个人都会走向虚无,只有极少数人能留下自己的故事。有一句话说:‘不要留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就是这个意思,哥不值得迷恋,传说才值得留恋。所以,重要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故事。”
“我是谁?”——“我”是“我的故事”。
“每一个人在此生,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建构自己。”讲到《哈姆雷特》最后一幕,哈姆雷特死去时对霍拉旭说:“你倘若爱我,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他说,人不怕死,怕的是不留名,不留名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故事可说,有好的故事,就是好的人生。

讲到《野草·过客》中的片段,一个老翁问过客:“你叫什么名字?你从哪里来?你什么时候开始走起?你要往哪里去?”他直言,这些问题全部无法回答,又全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如何讲好我们的故事的关键。
“纵观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会惊讶的发现,每一个历史事件或人物都值得被写成史诗、悲剧或抒情诗。可他们都消逝了,只留下淡淡的痕迹。”或许历史中有很多伟大的人,但他们的故事无法流传,而像汪伦那样,“不过请李白喝了几次酒,吃了几顿饭,就留名千古”,也正说明了故事的本质——“故事就是身份,故事就是经历,故事就是生命。讲的不好的故事,流传不下去的故事,都等于没有故事。”
“把我们的路走远一点,把故事将精彩一点,形成独一无二的故事。”因为,“我们对一个人的尊敬,是对他叙事的尊敬,对他独一无二的经验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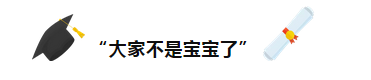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顾晓燕老师走上讲台前,同学们的应援已经躁动起来了:“粉丝”为“晓燕姐”举起了告白灯牌,晓燕姐的笑声和准毕业生们的哄闹已经让气氛从弱水先生课堂上的沉思转向了一片轻快活泼。

“我很久没有走进教室紧张的感觉了,但今天有。今天我想起了我念书的时候喜欢坐在最后一排,觉得老师看不到我在做什么,但是自己当了老师后,其实看的一清二楚;我还想起了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是我博士阶段的最后一堂课,之后我再想上学,也没得上了……”一开始,晓燕姐的“碎碎念”就让大家欢笑不断。
“我今天要讲的,是未来你们工作时会遇到的问题。”晓燕姐的课堂,在告诉大家,“我要到哪里去”。
“放低心态,放低身段,做好准备从最简单、最基础的工作做起。”时常会有学生跟她交流,自己去到了很好的工作单位、制作公司,但是做的却是最外围的工作,感觉和自己的设想有落差。晓燕姐说,“这是社会上的正常的状态,不要因此很失落。”
在浙江卫视工作那几年,顾老师的头三个月工作无比简单和“无用”——抱三脚架,可是电视台的前辈却告诉她,从她做这件小事,就可以看到她的特质。“哪怕是最基础的工作,老师也是在看着你的。做任何觉得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聪明、勤奋、用脑子,都会产生想不到的结果。哪怕是订订书机,会思考的人也会做的不一样。”
初入职场,除了要沉心静气、愿意去做基础的事情,也要勇敢争取机会。“曾经有一个老师告诉我,这个行业‘两年出成绩’。”顾老师正色道,“大家都不是宝宝了。在这个行业,两年没有做出成绩,人才那么多,机会那么宝贵,如果不能充分做好准备,真的就会浪费和错过机遇。”

从象牙塔出去,还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这个世界精彩纷呈,也可以说光怪陆离。”尤其做新闻记者,接触到的事情“无奇不有”。顾老师讲述了几个刚工作时让她感受到社会“无奇不有”的故事:做违章建筑牵扯出两个家族的世代恩怨;做正面宣传,结果采访对象是村里请来的剧团演员;采访对象八次说出完全不同的事实……“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奇怪的,如果你觉得奇怪,一定是你了解的不够全面。”
在走出校园,真正成为“社会人”后,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工作的繁忙、经济的压力、对固有认知的挑战……但是,“人生的任何经验,都会在未来给你非常大的帮助。哪怕碰到困难、受到委屈,一定要扛得住,并把它视为人生的财富。”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回想过去,晓燕姐说,“记得住的事情,都是糟心的事情。”但这些糟心的事情,如今在她的生活中,却成了最珍贵的回忆和最宝贵的经验。
“除了生死之外,没有更大的事情了。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坚持住,就成长了。”
“最后,无论遇到什么都是成长,一定要以善意和阳光看待这个社会。”
14级的方杨勇同学为她献上了鲜花,鼓起勇气说出了最真挚的告白:“说出这句话很艰难……还是要说,在我心目中,你比大甜甜(方同学的idol:景甜)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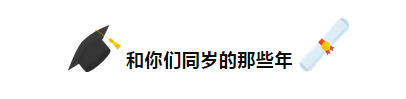
15:30,李红涛老师开讲了。一张口,语速依旧×2.0。
“我做学问没有一瓢先生(陈强老师)做得好,讲段子当然也不如千娇百媚晓燕姐,今天和大家讨论的问题可能是相对无聊的一个问题。来讲最后一课的时候,我会想在传播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你们的最后一课,但这其实不是我的最后一课,我的最后一课可能还需要二十年,这是我们之间的第一个错位;第二个错位,我38岁,你们还是18、19、20多岁,我被归到了中老年行业,你们还年轻。时间差别意味着什么呢?在传播学上来说,我们的距离一直存在,这是空间上的距离。对于这个空间距离来说,我从来不喜欢站在这个地方(讲台),我希望稍微向你们靠拢一点,但时间上的距离是无法靠拢的,而且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大,等到我58岁的时候,我面对的学生还是18岁。

“所以我在想人和人之间其实是无法沟通的,我今天想做的工作,除了从空间上向你们靠拢之外,还有在临别之际,稍微贡献一点弱水老师所讲的‘讲述我们的故事’,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由此,我会讨论1999-2006,我的私人阅读史。因为1999年到2006年,是我跟你们同龄的那个时段。我想回去看看二十年前,那么天真和naïve的时候,我在干什么;我想回顾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我大概读过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如何被过去塑造的。”
大学是什么?李老师最喜欢约翰威廉斯在《斯通纳》中的解释:“对那些被驱逐者、残废者来说,大学就像是一座收容所,一个远离世界的庇护所。”

1999年的夏天,他从牡丹江出发到北京,再用32个小时到了重庆,进入西南政法大学。“吃着地沟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
“我曾经痴迷过今天看起来不该痴迷的人,把这些讲出来或许很羞耻,但也是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
“那是一个在校园里面靠写诗就能被半个校园知道的时代。”他记忆中非常深刻的一本书是北大才子余杰的《火与冰》,“我不记得这是不是大学读的第一本书,但我清晰的记得读完之后那种激动的心情。我写了一篇书评。”也正是由于这篇书评,他加入了《新报》——一份油印的杂志,校园杂志的时代,这本杂志在重庆赫赫有名。两年之后,成为了主编。
从《火与冰》出发,大学时代的他开启了新的阅读探索:从钱理群到鲁迅,再到福柯。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书扉上,他写了一句话:“从这里,我开始寻找精神之父的不息旅程。”

现在念这句话我起了鸡皮疙瘩,你无法正视自己曾经是这么愚蠢的青年。说回正题,读鲁迅给了我两个影响——一是成为了鲁迅的小粉丝,二是想成为鲁迅那样的人。所以我后来写了很多时事评论。”那一时期,他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位老先生却告诉他,“你不应该去念现当代文学,你应该去念传播学,现当代文学已经死了,传播学还活着,你应该去关心活着的现象。”一语成谶。
“我大概花了大学三四年的时间说我不要读新闻传播,我的心思都在现当代文学,但现实一下子给你一个公费保送的机会,那我接受。研究生阶段,我爱上了传播学。”
2005年,因为一本书——《超越西方霸权》,他似乎“如梦方醒”,看到了传播学的魅力。最终他来到香港城市大学念博士,而这本书的作者——李金铨,成为了他的博士生导师。
“人啊,都在雅俗中。”
那么,“江湖再见,或者相忘于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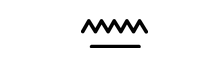
2018年5月27日,16:00
田家炳书院204,45名学生,3位老师。
最后一课,下课了。
离别是为了更好地相见,
祝2018届毕业生扬帆起航,前程似锦!

文 | 汪 涵
图 | 蔡雯雯
编 | 张鑫